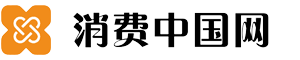一边,倦怠、佛系、躺平……互联网上,越来越多表达“无力感”的词汇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标签。
另一边,经历5年的走访后,黄灯在《去家访:我的二本学生2》中写道:“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,一种被遮蔽的力量,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复苏。”
透过黄灯的眼睛,在《去家访》中,我们看到了许多普通孩子的成长。神奇之处在于,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,真正步入广袤大地,走进他们具体而稠密的日常,互联网上关于年轻人的标签就会被一个一个地擦掉。
我们将看到,在社会的激流和现实的夹缝中,这代年轻人仍可以通过建立丰富而多元的链接,于家庭的托举与个体的奋进中,找到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法,活得踏实、充盈、从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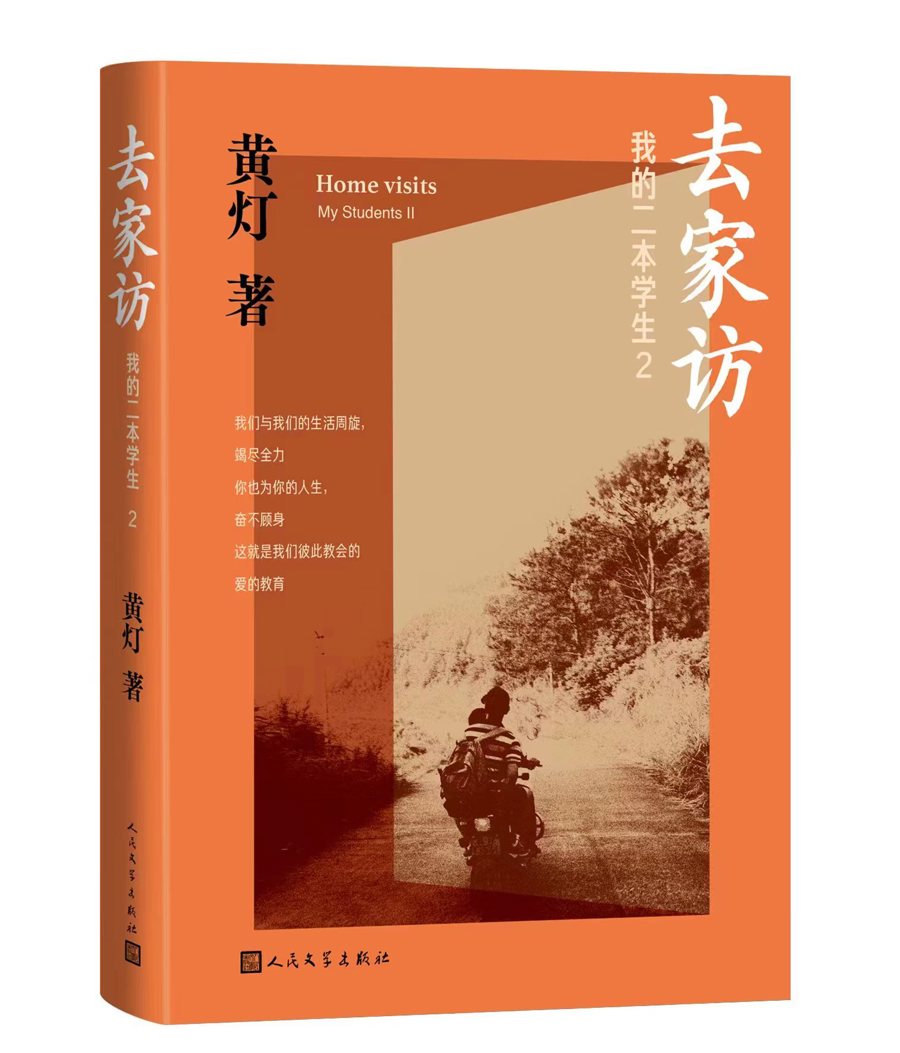
牵引我的,是一种朦胧的直觉
上书房:您之前那本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反响很好,许多人是通过您才关注到“二本学生”这个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的,他们形容您的写作像“一盏灯”。我很好奇,“黄灯”是您的真名吗?
黄灯:很有意思,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我出生于元宵节,在我的家乡湖南有“三十的火,元宵的灯”这个说法,所以父母给我起名叫“黄灯”,“黄灯”真真切切是我的名字。
上书房:冥冥之中,似乎与您的教师职业有所呼应。
黄灯:也许有一点。其实,每次走上讲台,我都感到兴奋,一看到学生我就很开心。到现在我都记得刚到大学上的第一堂课。那是在大一新生军训之后,当时我有很长时间备课,也准备了很多话题。因为第一堂课的课程内容是应用文写作,课本相对枯燥。当时,我站在讲台上,发现底下的学生们都特别认真,他们的眼神特别纯洁,带着些好奇,眼睛睁得溜圆,笑嘻嘻地望着你,能明显地感觉到刚高中毕业的孩子们那种憧憬美好的样子。
上书房: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出版后,也收获了许多教育界专业人士的关注,你和他们有交流吗?
黄灯:从我的视角看,我进行的是单纯的非虚构写作,但一些研究教育学的老师告诉我,在教育学的视角下,我做的事情叫质性研究,是很有学术价值的。尽管我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可供分析的框架,却反而更有一种专业交流的感觉,我好像可以和他们彼此关注、共同探讨。
因为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出版,我开始能够与许多具有现实关怀的学者进行交流,这让我受益良多。比如,北京师范大学的程猛老师出版过一本书《“读书的料”及其文化生产》,他站在教育学学者的视角对年轻人做出了分析;还有北京大学林小英老师写的《县中的孩子》,她关注了县域教育的具体情况;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施雨丹老师、华东师范大学的田雷老师……这让我们可以从很多视角认真地看到这些孩子,这很重要。
上书房:《去家访》可以看作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延续吗?
黄灯:确切地说,直到写完家访部分,我对二本学生的叙述,才有一个完整的表达。其实,在我原本的设想中,就是包含了校园视角和家庭视角的,后来实在是因为素材太多,为了叙述的流畅和可读性,我分成了两个部分,也就成就了两本书。当然,这也给了我更深入地去挖掘和了解的机会。
上书房:《去家访》的写作跨越了5年,但其实素材的收集从更早就开始了?
黄灯:可以说从我教课起就有了,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。一开始,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将这些东西作为写作素材来进行收集的。但我有一种直觉,觉得学生们身上有很多东西特别宝贵,舍不得丢掉或者忘记。
回想起来,我一方面感到应试教育好像把孩子们都掏空了,他们在考试中耗费了太多元气,变得缺少活力;但另一方面,在与他们的交谈中,在他们的写作中,我又能隐隐感觉到他们暗藏的力量。可能正是这样的矛盾,让我隐隐又产生了一种直觉,不自觉地也就留下了很多东西,而它们也不负众望地成为完整故事的一部分。
上书房:书中有好几名学生是主动邀请您去家访的,您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?
黄灯:我很喜欢和同学们探讨问题,一些之前没有被认真探讨过的问题,例如,你们为什么要读书,读书的目的是什么,知识究竟是什么……有些问题我会在第一次上课时就提出,而学生们会很快进入思考和讨论。也许正是这些问题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
对这些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既有憧憬,也感到迷茫。此前,他们一直埋头于书本知识,应付考试和作业,但对读书本身想得很少。我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讨论,并不指向什么标准答案,而是去寻找自己读书的真正价值。
上书房:“家访”这个词似乎已经很久不出现在现实教育的语境里了,当您见到学生家长的时候,他们会不会有点意外,您会不会有点局促?
黄灯:刚开始会有,但因为我的年龄和学生父母相差不大,我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记忆,所以很快能聊到一起。
其实,更多时候,家长们要么不在家,要么腾不出时间和我进行专门的交谈,所以我和他们的谈话会发生在各种地方、各种时候——红薯地、猪栏边、摩托车上;铡猪草、织渔网、修单车时……我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属于同一个时代的烙印,生出别样的默契,因此,常常一见如故,并没有什么隔膜。
上书房:你们一般会聊些什么?
黄灯:我们之间的交谈更像是熟人之间聊的家长里短,不会有太多的规划设计,只不过出于教育者的直觉,我会对家庭教育格外留意。
例如,我和早亮妈妈的闲聊大多伴随她每天的劳作,重点则是她在教育上的明确原则——“不娇生惯养”。由于爸爸出海、妈妈卖豆腐,家务繁重,早亮从小就要陪父母干活,哪怕是高三,应季农活时令一到,他一样要投入劳作。我了解到,正是在这样的培养下,在课堂上文弱、缄默的早亮,可以麻利地收红薯,快速地制作出一只美味的鸭子。
上书房:这次家访的经历,有没有改变您对教育的看法?
黄灯:我感到,在学校教育之外,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事实上构成了一幅具有层次感的教育图景,其中的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对于人的成长而言,我们不能只关心学校之内的世界,学校之外的世界是有很多宝藏的。
另外,在家访的过程中,也有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例如,在绩优主义的社会考评体系中,我们如何避免无休止的内卷;教育如何激活个人的直觉与勇气,让“工具的人”回到“完整的人”;作为教育者,我们能否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,给成长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;社会如何在评价体系愈加单一的现实中,帮助年轻个体确立自我;等等。针对这些问题的我的思考,我想,已经散落在书中无数的细节之中了。
上书房:您之前在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过,普通院校的学生和名校学生有没有区别?
黄灯:当然有。从整体来说,名牌大学历史悠久,积累深厚,学校的学术氛围更好一些。而现在的大部分二本院校,都是由以前的专科学校合并而来的,根基相对浅,学生没那么淡定从容。
上书房:您所说的淡定从容具体指什么?
黄灯:淡定是一种生命状态,是相对没那么匆忙的状态。名校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关注度是天然的,但对大量的普通孩子来说,是经常不被看见的。尤其是当他们走出乡村、走入城市之后,他们身上的许多特质变得“不再管用”,他们需要尽快“抓住些什么”,以便找到自己的道路。
比如,他们可能更着急地去找实习岗位,或者更早地去准备考试。他们迫切地希望获得一些外在的、可见的标准来证明自己,以便获得外界的关注或者认同。
上书房:您在书中提到,很多学生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状态是不一样的,或许有以上这些原因?
黄灯:在今天的媒体语境里,可能觉得孩子考上个二本实在不怎么样,但事实上,对于这个孩子或孩子背后的家庭,甚至对整个村庄来说,都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。
这些学生,当他们在学校时,并不会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学生,或者说大学生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的。但当他们回到家里,无论是父母还是乡亲,对他们能读大学这件事情是非常在乎的,是非常自豪的。这种来自外部的认可,会让他们表现得更具自尊,更有力量感。
黄灯:我的很多学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。比如,黎章韬从小就跟着他的外公外婆在田里劳动,他对植物非常了解;罗早亮也一样,从小就干农活,田间、地头到处跑。其实,大自然、劳作等朴素的日常对孩子们的滋养是非常重要的。
还有就是家庭教育,家庭氛围的熏陶。比如,要热爱劳动,要能吃点苦,要关心国家大事,要懂得照顾家里的其他人……这种熏陶不是建立在说教之上的,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。一个孩子与现实世界靠得越近,他与世界建立的链接也就越密切,他的力量感就越强。
上书房:像您刚刚提到的很多东西,例如,大自然,劳动,人有的时候需要吃点苦……都是朴素观念,但对今天的另外一部分孩子来说,好像有些陌生。
黄灯: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了,绝大部分独生子女都住在城市小区的公寓房里,他能接触到的事物是很有限的。无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心灵层面,今天的孩子都被人为地切断了与许多东西的联系。
这种联系一旦被切断,是很危险的。因为,人的力量来自很多纽带与他的联结,并不是单一的。我们常说,以前的孩子很皮实。为什么?因为一根纽带断了,还有另外一根。爸爸妈妈打了我一顿,但是爷爷奶奶会给我糖吃,或者我跑到外面去撒欢,和兄弟姐妹打闹一下可能就没事了。当孩子们面对困难或者遭遇冲击时,他们是有缓冲地带的。
上书房:家庭的确是个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您笔下有好几名学生,家庭状况非常艰难,但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。
黄灯:真的没有。《去家访》里面的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会去责怪自己的父母或者家庭。与之相反,他们更愿意去理解家庭的处境,并且想办法去解决。
人无完人,更何况是一个家庭。没有一个家庭是完美的。如果每一个小孩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事物,那么很多问题是可以归因于原生家庭的,但如果站在整个家庭的角度呢?家庭是一个整体,孩子并不只是处在一个“被给予”的位置,家庭成员之间其实是相互滋养、相互支持的。
现在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提出“断亲”——觉得自己的家境不好,为什么还要把我带来这个世界?在这里,他们都假设了一个前提,那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应该享受某些东西的。但很多人忽略了生命本来就是很宝贵的,不论家境贫穷或是富有,我们都需要在相互交融的生命体验中去支撑,去生活,去爱。
多点耐心,让年轻人恢复弹性
上书房:家访之后,学生们在您心中的形象是不是变了?
黄灯:其实,我最早对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整体去向是感到悲观的。我感到他们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逐渐失去元气,也担心他们在面对日渐激烈的学历竞争时失去勇气。
但后来,我会形容他们是“内心柔软、感情充沛、充盈着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”。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在课堂上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的细节——举着火炬走上学路、谈论海子的夜晚、三捆写到没墨水的圆珠笔芯、扶着中风爷爷缓缓前行的脚步……我清晰地感知到了父母的生计、劳动的历练、祖辈的陪伴、同伴的相处是怎样影响他们并给予他们力量的。我感到这些纽带是有力量的,而生命个体又是极富韧性的,它们在一起时会产生生命真正的重量,能够抵挡甚至化解一些时代的问题。
上书房:但对很多毕业于二本的学生而言,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,他们的努力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看见,比如,当他的简历和另一份名校生简历摆在一起的时候。
黄灯:对。正因如此,我才更有必要把二本学生的故事讲出来,呈现出来,表达出来。
在写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后,我接触到一些媒体、用人单位和企业老板,他们时常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以后招人的时候也要给那些二本学生一些机会,不要对他们有偏见,有成见。”但在这本书出现之前,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更要把二本孩子们的努力表达出来,只有让别人看到,才会有得到理解的前提和基础,才能为他们打开一些可能性。
上书房: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焦虑、压力那么大?
黄灯:为了拿到一个大学文凭,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付出太多了。在家访过程中,我看到太多不计回报的付出和竭尽全力的托举,一个年轻人的背后不只有自己的梦想、前途与追求,还有他的家庭,以及这个家庭日复一日的劳作。这时,他如果没任何要求就不正常了。社会应该理解他们的需求。
我们要给他们机会和时间,让他们能够换一个角度来观照人生。就像我当年下岗,文凭完全没用,我当时不过就是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下岗工人而已。你看,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。
上书房:换一个角度观照人生?
黄灯:对。我发现,现在的孩子们都不太自信。其实真的要相信自己,相信自己能够在社会上立足,不要因为感觉自己没有存在感就轻易放弃。
上书房:自信好像没那么简单。
黄灯:但也没那么难。我在广州老城区住了好多年,日常跟那些做各种各样具体工作的人联系很多,卖菜的、修鞋的、做理疗的、百货商场售货员,我会观察他们是怎么立足社会的,因为我的学生是大学生,他们的就业无非就是怎样立足社会,所以,我去观察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人,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生活的。其实,当我们深入了解了这部分人的生活之后,对大学生的前途命运的担忧就会变得不那么必要了——只要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,就能够活下来。
上书房:但不同时代的年轻人,感知是不一样的。
黄灯:的确。作为一名70后,我的青年时期恰好处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,处在中国厚积薄发的时代,毫无疑问,我们这代人是从中受益的。
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,社会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不确定性在不断地加剧。从表面上看,这是宏观层面的变化,但对个体而言,就是作用于他们人生发展最关键的一些因素在变化。
时代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,它会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的具体生活甚至个人命运中。我们时代的很多经验,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,并不适用。但也正因如此,我们需要去聆听他们的心声,鼓励他们去尝试,去发现,给予他们容错的空间。
上书房:在保留容错空间之外,社会的关注点也不能继续陷入“绩优主义”的单一评价里。
黄灯:是的。今天的年轻人活得不容易,我们的社会标准应该更宽容一点,我们的评价机制可以更有弹性一点。社会不能将年轻人看作“工具人”,因为随着时间的累积,工具只会不断磨损,但人会不断成长,可以积蓄力量。
我觉得只要做到这几点,年轻人很快就可以恢复活力,他们可以很快焕发蓬勃的生命力,迸发无穷的创造力。年轻人就像野草一样的,只要给他们一些雨水、阳光,他们就可以长得很好。
未来的发展,还得靠年轻人。因此,我们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,和他们一起直面真实的社会,抵抗生命的惯性消耗,帮助他们尽可能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,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生命场景中,以下蹲的姿态,激活生命,保持生命的韧性与弹力,让他们继续保有可持续的“起跳”能量。